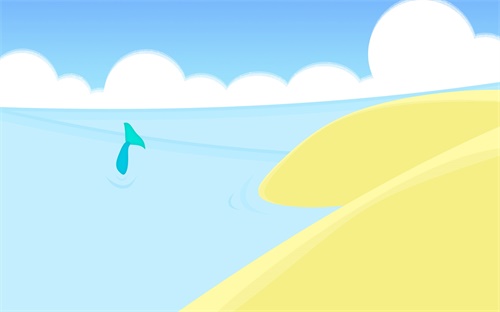这些骨骸均为非驯养动物。后来,气候逐渐变冷,不少喜热动物逐渐南迁。(洛阳博物馆出土展品)西周的时候,中原应该有“兕”这种动物。殷商之时,中原一带温暖潮湿,大量亚热带甚至热带动物活动于此。由此推断,甲骨文的“兕”,所指的,就是后来被称为“犀”的这种动物。
古文献中常出现大兕这种动物,具体是什么?
“兕(sì)”这种动物,并不那么神秘,应该就是犀牛——更早的古人管“犀”叫“兕”,稍晚的古人称“兕”为“犀”。《说文》曰:“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坚厚可制铠。象形。”段玉裁《注》:“野牛即今水牛。与黄牛别。古谓之野牛。……郭注《山海经》曰:犀似水牛,猪头庳脚。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清代著名训诂学家郝懿行考证说,“三”字衍,就是说,兕非重三千斤而是重千斤。
有人说,《山海经》是最早记载“兕”的古文献。这就错了。最早记录“兕”的,是殷商甲骨卜辞,而且不是一版几版而是不少版。比如,“《合集》37398”卜辞记载,帝乙时捕获一只白“兕”,别于通常青色,以为珍奇,遂刻辞记此事于“兕”头骨。在当时,“兕”作为凶猛大型野兽,捕获大约不易。所以,多版卜辞记载“擒获”的“兕”常为一只两只。
但也有多的时候。编号“《合集》33374”卜辞记载,商王某次狩猎“允擒十兕”。“《合集》10308”卜辞,则记录“获兕十一”。还有捕获更多的记载。“《屯南》2857”卜辞,“获兕三十又六”。最多的,是“《合集》37375”卜辞,“擒,兹获兕四十、鹿二、狐一。”(记录获兕四十的甲骨,《合集》37375)由此可知——第一,商末的时候,中原一带的“兕”数量不少。
胡厚宣先生在《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一文中,引一条卜辞说,商王狩猎曾追逐百余只“兕”——“囗子卜,囗,贞王逐百兕,阱。”第二,一次捕获三十多只、四十只大型的“兕”,亦可见当时商王狩猎规模之大,技能之高超。卜辞中,只记载捕获过“兕”而无“犀”。目前释读的卜辞,共载有九种狩猎捕获的“哺乳动物”,为“虎、象、兕、豕、鹿、麋、狐、兔、麑”。
(篆体“兕”字)但考古中发现的殷商狩猎哺乳动物骨骸看,则有十九种——为:狐、貍、熊、乌苏里熊、獾、虎、豹、猫、鲸、黑鼠、竹鼠、田鼠、兔、獏、犀牛、肿面猪、猪、獐、鹿、麋、扭角羚、象、猴。这些骨骸均为非驯养动物。上述卜辞记载的九种猎获哺乳动物中,唯一未见于考古发现的,是“麑”。请注意——甲骨文中未见“犀牛”的“犀”字。
但考古中发现了十余处“犀牛”骨骸遗存。由此推断,甲骨文的“兕”,所指的,就是后来被称为“犀”的这种动物。(甲骨文“兕”字)从文字学角度说,“兕”“犀”属于“叠韵”。“双声叠韵”是汉字孳乳的规律之一——“双声”指声母相同;“叠韵”指韵母相同。小篆“兕”字,一定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的;“犀”字很可能在周代由“兕”孳乳而产生。
殷商之时,中原一带温暖潮湿,大量亚热带甚至热带动物活动于此。塞北张家口的商代遗址中,亦曾发现大象遗骸。据徐中舒先生考证,河南代称的“豫”,其左边部首“予”实为“邑”之省略,本义是“大象之邑”。后来,气候逐渐变冷,不少喜热动物逐渐南迁。至战国时期,韩非子说,黄河流域一带很难再见到大象了。(洛阳博物馆出土展品)西周的时候,中原应该有“兕”这种动物。
所以,《周礼·考工记》说“兕甲六属”,“兕”皮被用来作铠甲。春秋的时候,“兕”在中原仍未消失。《左传·宣公二年》载,宋国的华元自夸说,宋国“牛皮则有,兕虎尚多”。这一年,是公元前607年。宋国的国度,在今河南商丘。学者们考证《山海经》,其最初应为西周王室的舆图档案,后来外流于世,经过不止一人亦非一次的补缀编纂。
特别是《海经》部分,既纳入楚地山水风情,又吸收海岱舆况人文。《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史籍载,舜葬于“苍梧之野”,在湘南九嶷山。说“兕”活动于“湘水南”,与战国末期的气候条件应该相吻合。《后汉书·章帝纪》载,蛮夷献生犀白雉。公元50年之后的时候,中国的南方还有犀牛活动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