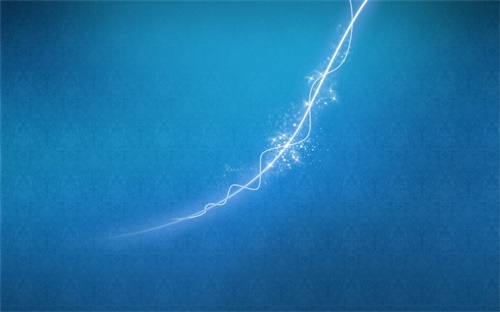作者:安徽枞阳县名师钱新华祖母驾鹤西去已有廿余载了,然而,她老人家留给我的那只玉鐲儿,一直静静地住在那只小巧而锈迹斑斓的锡盒子里面。或许这就是祖母灵魂化身后的寓所。每当我沉下心来,忘掉人世间的一切时,眼前便浮现出祖母晚年生活的一个个镜头:一座老式合六间农舍的门楣下,摆放着一张早已褪去色泽的小木椅子,祖母那苍老的身子倚靠在椅背上。
上身还是那件蓝士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流行的一种天蓝色的棉质平布)老式收襟褂子,下穿黑中微微泛着白底子布纹的大脚裤,浅黑色的木拐杖斜靠在她的身旁,夏南风吹乱了她的花白头发,浅绿色的玉镯子在腕关节处时隐时现,摇曳着淡绿的光,失去光泽的双眼平静地遥望着门前绿浪翻滚的稻田,嘴蜃微微张开,喉咙深处似乎低吟着一支轻柔忧伤的小曲。
一切表明,她还在迷恋着早已逝去的幽远岁月…… 这只镯子,倒也算不上是什么名贵之物,但它却真实地记录着一段珍贵的家族繁衍史。 这是当年祖父刚进入成年,在订婚时,馈赠给祖母的聘物。它出自民国年间,江南某地民间艺人之手,到了上小学的孙子这一辈该是第五代了。每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盒盖,掀起覆盖在上面的红丝帕,目睹着这只玉镯儿,便油然地想起自己上学发蒙前的欢乐的时光: 夏天夜晚,仰卧在凉床上,尽情地享受着祖母手中芭叶扇的阵阵清凉。
月亮如金黄色的香蕉悬在西南天际,星星眨巴着眼睛,与我一起快乐地聆听祖母吟唱着古老的枞阳童谣:“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打麻将,嫂嫂起来打鞋底,妈妈起来炒炒米,炒给小儿打打咀(枞阳方言音ji)……”记得最后那句词儿,是祖母用那只戴着玉镯的手轻轻地叩了几下我的小屁股而结束了哼唱。 有时,我象一只小懶猫似的依偎在她的身上,头枕着她的大腿,转动着她腕上的镯儿玩耍,并闹着也要戴镯子。
祖母见了,忍不住地笑着说:“这玉箍现在还不能给你,须等你长大了,娶了个花老婆,才能归你。”说着说着,又唱起了我不太懂的歌谣:“玉镯儿手上戴,吹吹打打把堂拜。拜完堂掀头盖,原来是个小妖怪。”后来才懂得歌词的意境与旋律都很优美,祖母的嗓音却有些暗哑。 1993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祖母走完了她那八十五载沧桑岁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如今,我欲见祖母,唯有这玉镯可帮我。我只要将鐲儿拿到亮处,对着光,便能见到镯子里的那几根如针线般粗细的血红色“筋脉”。再借助放大镜,还能感觉到血脉里的“血液”是流非流,血液余温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尽。这或许是祖母在经历了长达近七十载的岁月过程中,血脉末端在时光不断地磨合作用下而发生的一种微妙变化:人体毛细血管被植入镯内成活、生长而形成的奇迹。